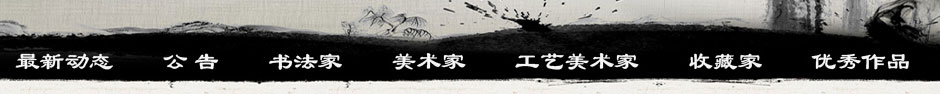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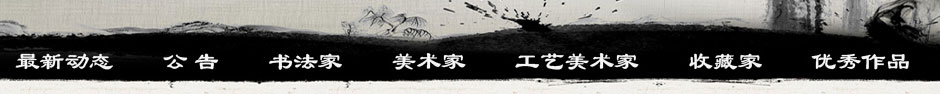
余險峰在大學學的是物理無線電專業,和書畫藝術相去不啻十萬八千里。他常感慨道,自己一生所學的并非自己所愛好的,所干的又并非自己所學的,而與自己終身相伴、被視為第二生命的書畫藝術,卻沒有一天得到專業的培訓。令人難以想象的是,正是一天也沒有受過專業培訓的書畫藝術,卻成為他一生最大的驕傲。 余險峰書法從米芾入手,得其圓勁。后又上溯二王,且廣泛吸納陸柬之、懷素、張旭、蘇東坡、黃山谷,以至明清諸大家,博采眾長,而出自家面目。他不再執著于字形,收斂了米芾的鋒芒,更強化了長線條的運用和鐵筋般的線條韌性。他的書法注重大效果與整體氣息,因用筆的節奏變化而自然生成章法。他還善于把繪畫的墨法引入書法,做到筆墨相融,潤燥相生,蘊五彩于黑白之中,從而增強章法的起伏跌宕。 我們不難想象,以余險峰的書法功底,將他的書法線條引入國畫,再加上他長期以來對傳統文人畫的研習、揣摩和書畫以外功夫的長期積淀,無論山水、花鳥,抑或人物,其成功幾乎是毋庸置疑的。早在1997年,當代著名書畫家、書畫評論家梅墨生在與余險峰的通信中說:“大作書法圓渾勁健,有書卷氣,不似今人滿紙縱橫,一片狂野,佩甚,功底在米襄陽、顏平原之間;而畫作則煙云迷離,有蒼茫境界;花卉則清雅。”梅先生當年的這番評論,可以令我們想象10多年前余險峰書畫藝術已具有不凡的面目,其作品所具有的文雅之氣已經引起專家的關注。評論家徐錦斌以極大的熱情在《古典語境下的優雅》和《審美生存的心靈圖景》等多篇評論中,對余險峰的書畫藝術做了深入的評析。他認為余險峰的中國畫“精致、沉靜、淡泊、內斂,有他的孤高冷峭,更有他的仁慈惻隱,無疑寄寓了他的審美理想,是他追求自由、慰藉心靈、關懷自身、安頓生命的重要生存形式……” ?? 余險峰對古典詩詞懷著深深的敬畏之情,以為是中華傳統文化的精華。他所寫的舊體詩作品不多,但均屬于有感而發,且字字珠璣,頗多佳句。如《北戴河懷古》中的“連天一勺乾隆水,傳世五言蕭顯情”;《過姜女廟》中的“姜女有知應不哭,長城萬古壯中華”;《紅螺山行》中的“半縷浮云隨意住,滿渠清響洗心空”;《荊溪閑居》中的“淺橋親野水,瘦月探初梅”;《客至》中的“清風翠竹送蟬鳴,夢覺客來茶正馨”;《答友人》中的“一任斜陽好,何妨綠雨寒”……字里行間無不透著一股大氣、雅氣、清氣和靈氣,讀之常常令人有一種禪的感悟。在泉州展覽的開幕式上,93歲高齡的福建師大中文系資深教授、著名詩人、書法家陳祥耀老先生以其雄強蒼老的書法,寫了一首五絕:“法書米海岳,禪畫董玄宰。何處問殊同,心燈筆底在。”來評價余險峰的書畫。 書畫評論家歐孟秋在《自由心靈的抒寫——<險峰翰墨>讀后》一文中這樣寫道:“藝如其人,人品、氣格與意志對藝術生命活力的決定意義,人所共談。我深切體會到,在頗富實力的書畫家中,險峰兄的智力背景、精神境界都是令人欽羨的。”著名書法家趙玉林老人也說:“余每讀險峰書作,則常有如聆聽一曲雄渾壯美的樂章,為其強烈的節奏、無窮的變化和充溢于字里行間的陽剛之美所陶醉、所感染。” 余險峰的書畫先后在加拿大、日本、新加坡、菲律賓和香港、臺灣等地區展出,流傳于美國、英國、加拿大、新加坡、日本等地。先后有專集《余險峰書法》、《險峰翰墨》、《余險峰書畫》等出版。其傳略被收入《當代中國書畫家大辭典》、《中國歷代書法家人名大辭典》、《中國文藝家傳集》、《世界名人錄》、《世界華人文學藝術界名人錄》、《跨世紀著名書畫藝術家精典》等數十部辭書。 |